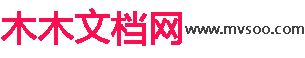摘 要: 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媒介成为我们认知灾难记忆的重要媒介之一,媒介对灾难记忆的建构话题也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介生产出来的记忆文本,在主题上以自然灾害记忆与战争记忆的建构居多,在建构手法上着重于灾难记忆的再现与重塑,在研究走向上侧重于灾难记忆的数字化,而整体研究则呈现出重文本轻效果、突出个案研究轻宏观关照的特点。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1-0057-07
关键词: 灾难记忆;大众媒介;记忆元素;数字化记忆
人类发展进步史上,灾难始终如影随形,水、旱、虫、地震、瘟疫等各种灾害频繁发生。灾难对人类的打击别无二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倾向于通过“健忘”来修复心理创伤,使灾难的记忆一天天淡去。不过若缺乏对灾难记忆的重视,我们就会缺乏有效应对灾难的机制和能力,在每一次类似灾难发生时,我们都会像第一次面对时那样惊慌;而当灾难过后,我们又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安然。因此,一个社会究竟该如何记录和记忆灾难,这是每个“未来可能的受灾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媒介作为我们思考过去的最具影响力的记忆图式框架,不断改变着灾难记录与记忆的模式,在灾难记忆的保存、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中,大众媒介对灾难记忆应如何建构,人们应如何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灾难记忆,灾难记忆又如何影响社会等等,这些有关媒介与灾难记忆建构的问题就随着媒介的发展更受到学界的关注,从新闻传播学的路径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探讨也就随之而增加,不过相较于其他领域对灾难记忆研究的热闹,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稍显冷清。
一、灾难记忆研究概述
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赫(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是社群对过去的建构,是共同创造的结果,社会性是集体记忆的核心特征〔1〕。随后集体记忆研究西进美洲,东到日本,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记忆之所以如此被关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是因为历史的加速度造就了记忆与历史的决裂〔2〕,这为多学科的记忆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灾难因其在生物进化和人类历史上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自然进入人类的共同记忆,成为了国内外集体记忆研究者的焦点,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灾难记忆的概念、传承空间和记忆内容等方面。
在概念的界定上,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亚历山大将灾难记忆看成一种文化创伤,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3〕。事实上,这些“可怕的事件”的痕迹就构成了群体的灾难记忆。
这种灾难记忆又是如何传承的呢?人类学家樱井龙彦认为,灾难记忆通过口头传承、纪念物和仪式三种方式来传承并实现灾难的预防〔4〕。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从各个视角对此进行了阐释。李建平认为灾难文学作品可以传承灾难记忆,作家们以手中之笔叙述战争各面,努力实现由作家记忆向民族记忆的文化传播〔5〕;徐新建发现忧患传统如“多难兴邦”和“居安思危”这类文化认知能在地震灾害记忆中复归并成为华夏渊源历史记忆传承的可能〔6〕;夏明方认为对过去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是灾难记忆的一种传承方式〔7〕;洪淑苓认为民间艺人编唱的“歌仔册”既参考了新闻报道又加上了文学性的描绘,用劝善劝世的套语来引起受众的共鸣,达到了传承灾难记忆之目的〔8〕;杜辉认为公共博物馆由时间、空间和物质三个维度交织而成,与战争有关的体验在博物馆空间中被陈列,可以通过表征来完成战争记忆塑造和认同建构,进而“使战争记忆成为国家内在凝聚力的来源”〔9〕;邓绍辉则认为纪念日是重构战争记忆的重要空间形式,故设立国家纪念日极其重要〔10〕。由此可见,在学者眼里灾难记忆的传承实践是通过文学作品、民间传唱、文献史料、纪念馆、纪念日等“纪念场”进行的,从而达到再现灾难历史、悼念遇难者、铭记教训、提高灾难认知的目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记忆空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会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意图的影响,且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空间建构影响也不同〔11~12〕。
二、媒介与灾难记忆研究的兴起
正如沃尔夫坎斯坦纳(Wolf Kansteiner)所言,集体记忆研究的成果虽然丰富,但其理论与方法创新较少,研究视角相对局限,因此集体记忆研究应重视采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路径〔13〕,这为“媒介与灾难记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及价值所在。最早研究大众媒介与记忆的兰·凯尔特(Lang.Kurt)认为,新闻记者会援引历史事件来“充当(衡量当下事件)标尺,建立类比,提供解释”,以此汲取历史经验〔14〕。延续这一思路,埃迪(Edy,Jill.A)首次将媒体中的灾难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就瓦茨暴乱报道数据分析发现,媒体通过纪念报道、历史类比、历史语境三种类型对历史事件调用,能将“过去”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凸现往事意义,增进对现实的理解〔15〕。这些代表性研究证明了大众媒介在构建、重构及维护灾难记忆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为我们提供特定的历史叙事,强化和突出了相关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显示度和在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16〕,而且由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被用作意义相对固定的‘媒介模板’之后,也会影响新闻记者和受众对当下事件产生特定的感知和理解”〔17〕,故还可促使社会群体通过新闻叙述建构出他们自己的现实生存图景。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我们认知灾难记忆的工具之一。
各个领域的学者也都意识到大众媒介在灾难记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开始多种视角论证大众媒介对灾难记忆的建构作用、方式及影响。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认为,记忆的社会图式有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三种,其中大众媒介图式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和影视等艺术方式对灾害事件进行多种表述,从而形成一种历史认识来培养人们对灾害的应对力,而这种图式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主要的记忆图式。大众媒介“不仅是当代观念和价值的供应者,而且还是我们思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宗教圖式和政治图式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其影响力显然已经走向边缘了,甚至被迫在媒介图示下进行解释”〔18〕。亚历山大则进一步论证在“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让创伤得以戏剧性的表达,成为能唤醒受众创伤记忆的媒介之一。埃尔(Erll)更是感叹“文化记忆离开了媒介是不可思议的。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从想象”〔19〕。而王晓葵进一步看到了互联网对灾难记忆的影响,他通过分析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框架发现,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原本被尘封的灾害记忆大量浮现出来,其中民间传说框架和人性叙事记忆框架最令人关注,而且“作为权力记忆框架的补充和反动,民间传承框架和人性叙事记忆框架逐渐壮大,预示着灾害记忆建构的多样性、立体性格局逐渐形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