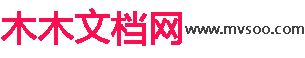摘要:古代小说中的韩愈是一个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同时又经过小说家发挥艺术想象力加以再创造的文学人物。伴随着两次被贬岭南的苦难经历,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复杂多样:有忠而见黜的委屈与命途多舛的怨嗟、士大夫失位的沮丧与英雄末路的惶悚,也有临危处穷的绝望与性命不保的忧惧、牵念家人的痛苦与心存魏阙的煎熬、渴求慰愍的凄恻与颠连无告的哀怆等等;其演进的过程也有一定的线索和脉络。至于韩愈在小说中变成一个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研讨古代小说中的韩愈形象与韩愈心态,对于开拓古代小说研究的领域,探索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的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影响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韩愈;流贬心态;历史影像;艺术真实;“韩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144—06
韩愈一生,可谓宦海浮沉,变幻莫测,却又不乏可圈可点的“人生大手笔”,颇富故事性和戏剧性,本身就是很好的小说的素材。所以,自中晚唐五代以来,韩愈便成为了小说家笔下的一个“出镜率”较高的人物。载录了韩愈故事的书籍,中晚唐五代时期主要有旧题柳宗元的《龙城录》,李肇的《国史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读的《宣室志》,范摅的《云溪友议》,杜光庭的《仙传拾遗》,王定保的《唐摭言》;宋代陶谷的《清异录》,刘斧的《青琐高议》,王谠的《唐语林》;明代王世贞的《列仙全传》,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旧题“唐瑶华帝君韩若云自撰”的《韩仙传》(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收录,一般认为应即明人托名所为),以及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等。其中,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始写湘子度文公事,自传体文言小说《韩仙传》则以洋洋八千余言的篇幅写了韩湘子前世修行和投生之后遇吕翁点化成仙,及其度化叔父韩愈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杨尔曾的白话长篇通俗小说《韩湘子全传》(又名《韩湘子十二度韩昌黎全传》)于明天启三年(1623)面世,成为古代韩愈题材小说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叙事最生动的集大成之作。
本文拟参照韩愈两次被贬岭南的历史,全面深入地探讨古代小说——特别是《韩仙传》和《韩湘子全传》中韩愈这个人物的流贬心态,分析这种特殊心态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合理性,并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小说人物韩愈的最终改变信仰、弃儒修真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并探讨文学人物韩愈的研究对于古代小说研究以及“韩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历史影像:复杂多端、百感交集的流贬心态
历史上的韩愈,自德宗贞元八年(792)24岁登进士第,十二年(796)28岁于汴州被辟为宣武节度使幕观察推官,十八年(802)34岁授四门博士,一直到穆宗长庆四年(824)57岁病逝赠礼部尚书。他为官30年间曾3次被黜,其中两次被流贬到岭南:一次是贞元十九年(803)35岁时以监察御史如实上奏
关中天旱人饥状,抨击群臣不言灾情,“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①,得罪了权臣,贬连州阳山令。在任一年,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至宪宗元和六年(811)43岁方始回京任职,前后历时8年。另一次即元和十四年(819)51岁时以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将加极法”,后“稍赐宽容”贬潮州刺史②,在任8个月,移袁州刺史,翌年(820)穆宗召拜国子祭酒回京,前后不满两年。两次累计近10年的流贬生活,给韩愈的人生平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但也记录了他戴罪南窜、流离穷处的苦难心路历程。
写到韩愈负罪南迁故事的古代小说,若论对韩愈流贬心态的表现,则刘斧的《青琐高议》、旧题“唐瑶华帝君韩若云自撰”的《韩仙传》和杨尔曾的《韩湘子全传》最为重要。其中,许多描述与历史真实基本相符,具体有5个方面,可谓复杂多端、百感交集:
一是忠而见黜的委屈与命途多舛的怨嗟。“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③,“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④——两次被贬,皆因忠直敢言,其内心的怨怅已经溢于言表。而在《青琐高议》(韩湘子作诗谶文公)、《韩仙传》、《韩湘子全传》等几篇(部)小说中,都有韩愈蓝关遇韩湘子冒雪前来相送,韩愈完成“云横秦岭家何在”全诗的情节。其中“欲为”二句,凸显出忠而见黜的怅憾,纪昀评“是一篇之骨”⑤。《韩湘子全传》中,韩愈还在避雪时口占《山坡羊》,其“命蹇时乖,忠心天表”之句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感慨。
二是士夫失位的沮丧与英雄末路的惶悚。《孟子·滕文公下》:“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又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韩愈既然以儒家道统自居,则其看重名位是自然的,以致有学者评价韩愈为人有“趋荣贪位”、“好博进”、“贪仕宦,……浑身俗骨”⑥的一面;岂料“朝为青云士,暮作白头囚”⑦,“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⑧——曾经的辉煌与得意转瞬即逝,眼前只剩下漫漫长路伴随着他这个落寞失意的“谪宦”远行。与此相近,《韩湘子全传》也写韩愈一向把功名视为生命,不仅自己汲汲孜孜,还刻意教育湘子通过读书博取功名,“改换门闾,光显父母,我方心满意足”。而流贬潮州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意外了,他简直懵怔了,“一路里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十分憔悴,比昔日在朝时节大不相同”;在秦岭蓝关“两泪交流”地叹道:“我韩愈尽忠尽孝,为国为民,只指望名标青史,死有余芳,谁知佛骨一表,弄得家破人亡,夫妻拆散。”身份地位的这种颇富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使韩愈简直无法接受,以至数度寻死未果。
三是临危处穷的绝望与性命不保的忧惧。《青琐高议》中,韩湘临别送韩愈一粒可御瘴毒的药,愈谓湘曰:“我实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但得生入玉门关足矣。”《韩仙传》写大雪中“从者二人皆遁去”,韩愈“独无倚待死而已”,“号呼百状”;《韩湘子全传》中韩愈口占《清江引》一词,有云:“听猛虎沿山叫。三魂七魄荡悠悠,生死真难保。”而在几篇(部)小说中都充当重要线索的那首“云横秦岭家何在”诗,其结句“好收吾骨瘴江边”更简直就是一份大限临头的个人“遗嘱”。韩愈将流贬潮州视为致命性的祸难,主要的还是因为潮州路途遥远、险恶,而限期极短,即便按期到达,潮州乃以往“推选此地者,无不哭泣告改”的“极恶烟瘴远方”,实难生还。⑨正所谓“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⑩;亦如韩愈当年《潮州刺史谢上表》所云:“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四是牵念家人的痛苦与心存魏阙的煎熬。韩愈流贬潮州途中,曾写下“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的诗句。潮州到任后,又上表唐宪宗,“诚惶诚恐”地表达了“恋阙惭惶恳迫”之情,希望其“哀而怜之”,使他重新“得奏薄技于从官之内”。这样的痛苦和煎熬也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在《韩湘子全传》中,韩愈落难离家之际,“泪出痛肠”,与夫人“难分难舍”;在蓝关路上,痛悔谏迎佛骨致使“家破人亡,夫妻拆散”,都表现了韩愈对家人的牵挂。而《韩仙传》写到韩愈第一次被流贬中拒绝云房(钟离权)、纯阳(吕洞宾)二翁要他抛弃“美官”而寻求“久世以长生”的劝诱;第二次被流贬中面对湘子“以勇退为劝”,或含糊应承,或婉言推阻,态度摇摆不定,都表现了韩愈“恋阙”的情怀和心理。
五是渴求慰愍的凄恻与颠连无告的哀怆。历史上的韩愈其人非常注重人伦亲情,不仅做到了“幼养于嫂郑氏,及嫂殁,为之服期以报之”,而且“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应该说,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当他自己蒙受祸难之时,自然也更需要和渴望亲情及友情的安慰。他写《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对“生平所未识”却“待我逾交亲”的新朋友“感谢情至骨”;其《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所谓“知汝远来应有意”,更饱含着一种人伦亲情的温馨与慰藉。而在小说中,韩愈与韩湘子就如同血亲父子。当年兄长过世,韩愈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抚养年幼侄儿湘子的重托。他“以母道”待嫂;嫂殁,湘子“抱负宿兴皆委於叔”,才得以长大成人(《韩仙传》)。因此,贬潮州“途中,公方凄倦,俄有一人冒雪而来。既见,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舍吾乎?’因泣下”(《青琐高议》)。同样的情节,在《韩湘子全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随着秦岭蓝关途中险象厄境的层见叠出(多为湘子与蓝采和法力所为),韩愈望眼欲穿地祈盼着侄儿前来相“救”。一旦侄儿来到眼前,韩愈则“抱住湘子,号陶大哭”,还埋怨湘子“如何早不来救”。显然,落到这步田地,韩愈更加渴望和珍重亲情的拯赎与抚慰。
二、艺术真实: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的重大转变
古代小说所表现的韩愈的流贬心态,也有与历史真实不十分相同之处。韩愈潮州治理鳄鱼之患,在中晚唐五代时期(即两《唐书》出现以前)的几件比较可靠的史料以及韩愈自己的诗文中,或者只字未提,或者语焉不详。但自张读的《宣室志》以后,小说中的“韩愈治鳄”便越来越神奇。先是直接影响了五代及宋人两《唐书》中《韩愈传》的撰著,其后直至《韩湘子全传》第二十二回“坐茅庵退之自叹,驱鳄鱼天将施功”,发展成以“治鳄”为中心,全面展现韩愈“治潮”的功绩。内容洋洋洒洒,包括韩愈到任即“升堂画卯,谒庙行香,盘算库藏,点闸狱囚”,并“张挂告示,晓谕军民人等”,遂有百姓禀告鳄鱼之患,又有人告状母亲失踪于河边(实是被鳄鱼吞噬)。如是铺垫之后,小说详细描述了韩愈在湘子的暗中帮助下成功治鳄的神异过程,艺术地表现了韩愈虽然坐贬穷海,却不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的士夫情怀和担当精神。
当然,古代小说所表现的韩愈的流贬心态与历史真实最大的不同,还是韩愈在贬潮州的途中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即由坚守儒家道统而排斥佛道,变为信服二教“不诬”;由热衷“金章紫绶”做官,最终变为“一心只望清修善地”。在《韩湘子全传》中,湘子的持续“外部施压”是韩愈思想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小说第十九回中,湘子向云房、纯阳两师请示“我叔父已往潮阳,正在路上”,“今欲吩咐值日功曹唤巽二起风,滕六作雪,一月之间,倏大倏小,不得暂止。弟子与蓝师两个,或化作艄子撑驾渡船;或化作渔父涧下钓鱼;或化作樵夫山头斲树;或化作田父带笠荷锄;或化作牧童横眠牛背;再化一美女庄招赘叔父受些绷吊之苦。……命蓝关土地差千里眼、顺风耳,化为猛虎,把张千、李万先驮至山中修行,止留叔父一人一骑走上蓝关,……待马死人孤,然后度他,……”而随着这些招法的不断施展,“备尝苦楚”的韩愈终于醒悟,发誓要“脱却藩篱,一心只望清修善地”,并且此后未见些许犹豫和反悔。
如果说《韩湘子全传》中韩愈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处穷历险而痛感人生苦楚、理想幻灭;那么,《韩仙传》中韩愈的转变则主要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内心挣扎最终信奉了仙道。相比之下,《韩仙传》中韩愈的转变有两个特点:
一是道路更加漫长。《韩湘子全传》写到湘子帮助韩愈潮州治鳄后,即施展“尸解”法术引导韩愈去卓韦山修道了;而在《韩仙传》中,韩愈的转变一直延续到回京、官复原职,57岁(历史上的韩愈57岁去世)时方正式接受湘子的度化回归仙界,“始有冲和之悟焉”。此时虽然韩愈早已结束了流贬生活,但毫无疑问,此前的不幸遭遇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苦难记忆,并深刻影响着他后来人生道路的抉择。
二是过程甚为曲折。《韩湘子全传》中韩愈的转变呈直线演进形态,基本没有反复和回转;《韩仙传》中韩愈的转变则呈曲线演进形态,一直是左右摇摆,甚至屡有反悔表现:秦岭蓝关遇大雪,人马疲惫,二从者逃走,幸亏湘子来救,韩愈“号呼百状,悲喜交集,始曰:‘子先言有验矣,予迷耳。’”可是当湘子趁机劝诱他跟着自己“以效长生”时,韩愈却以君臣之道及家庭伦理为由婉拒;潮州治鳄后,湘子“以勇退为劝”,韩愈表示“但得归见宗祖,即当随侍,任所之耳”,还发下如若反悔“天当殛诛”的“毒誓”;可是回京任职后,韩愈又要湘子“取进士”以证明神仙无所不能,方能“倾服之”并“从道”;甚至最后一刻,韩愈又认为“仙人不常见”,希望“老死于乡党足矣”,并请湘子体谅;直到一不留神被湘子用竹杖化形,尸解仙去,却因先前执迷不悟惹得上帝不喜,不将其赘于“上仙”之列,而是送至昆仑山“为使”,愈“方大悔”。两篇(部)作品中韩愈思想转变的动力略有不同,一个主要在于客观,一个主要在于主体,却正好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必须指出,在两篇(部)小说中,韩愈本是一位“谪仙”,到人间转世历劫后,为韩湘子所度,重新回归上界。这实际上是为韩愈的人生路向做了一个“顶层设计”,即不管这个人物被谪降在人间时信仰如何、经历如何,他最终都将脱离尘凡,返归仙班。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仙道人物生活方式的固有模式之一。例如旧题班固撰的《汉武故事》,就把东方朔描绘成因偷吃仙桃而被西王母贬降人间,后来又飞升回仙界的“谪仙”。类似这样简单的“大团圆”结局,从作者创作的角度来说,固然省去了许多烦恼,可是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以及人物的艺术魅力却通常是被打了折扣的。即是说,关键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在于过程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作为文学人物,《韩仙传》与《韩湘子全传》中韩愈的思想转变是可信的。这首先并非因为韩愈是一位“谪仙”,最终必然皈依仙道;而是因为他有过特殊的苦难经遇——流贬。两篇(部)作品中韩愈的转变都始于秦岭蓝关途中,就说明作为一个“流人”,身处沉浮宦海、炎凉世态的逆境之中,往往易于产生理想幻灭、人生无常的感慨和悔悟,出世之思与绝尘之想便只在一念之间。三国时的曹植,在其父曹操死后受到曹丕的猜忌与排斥,远就藩国,“常汲汲无欢”,故其《远游》诗云:“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此游仙诗所表达的正是“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曹植虽遭驱遣,但身为藩王,只要小心谨慎,量无性命之忧,却心生求仙的愿望,何况韩愈此去将是一个几无归望的绝地呢?而且,历史上的韩愈在生活中对于道教的态度本是矛盾的,既认为“神仙传说”都属虚妄,却也憧憬过“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的奇幻境遇。这说明,韩愈如果在被流贬的过程中像曹植那样产生了“求神仙”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两篇(部)小说中韩愈的转变之所以可信,还因为它们有一个合理的演进过程。《韩湘子全传》中,韩愈历经大雪、美女的考验,艄公、樵夫、渔父、牧童、庙祝、田夫等的点化,虽然惊悚、疑惑、教训接踵而至,却一直不愿回心转意,放弃去潮州做官。直到最后身陷绝境、性命不保时,才对着前来“救”他的湘子表示“情愿跟你去修行,再不思量做官了”。而在《韩仙传》中,如前所述韩愈的屡次周折和反复,使读者充分体认到这位“谪仙”平凡人的一面:他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藕断丝连,又对神仙道化抱着实用的态度。这就难怪他对修真学道左右摇摆、犹疑不决甚至出尔反尔了。
综上可见,古代小说中韩愈的流贬心态是复杂多样的。随着流贬事态的发展,它大抵是沿着下面的线索和脉络向前演进的,即:由怨怅忠而见黜、士夫失位,到忧惧性命不保而渴求亲情抚慰;到恋阙与隐退纠结、做官与修真矛盾;最后改变态度和初衷,信奉神仙之道,决然斩断名缰利锁,一心修道。
三、古代小说中的韩愈最终弃儒从道的文化解读
那么,小说中的韩愈成了一个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的人物,是否可以做出相应的文化解读呢?笔者试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做如下分析:
首先是主观方面。如上文指出的,历史生活中的韩愈对于道教本来持着矛盾的态度,这给人们演绎他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可供发挥和想象的空间。更何况与他同时的白居易还在其《思旧》诗中言之凿凿地声称韩愈死于“服硫磺”(“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又有五代至北宋人陶谷(903—970)的《清异录》记载韩愈喜食一种用硫磺末拌粥饭喂出来的公鸡而丧命。“服食”起源于战国方士,后成为道教求长生的修炼方式,石硫磺便是常见的用于服食的金石药之一。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韩愈服食硫磺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小说家们为之高兴的是这样的说法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果然,陶谷身后不久,在北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韩湘子作诗谶文公”)中,韩愈通过亲睹韩湘“夺造化开花”,特别是被贬潮州时亲历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预言,开始相信湘为“异人”,并由此承认佛道二教“不诬也”。这是中晚唐五代以来小说中的韩愈首次转变对二教的认识和态度,对于韩愈这个小说人物最终受韩湘子度化而返归仙班,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客观方面。一是小说中韩愈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可以认作是与道教的历来被统治者重视的大背景有关系。唐代是佛道二教兴盛的时期,统治者或信佛,或崇道,或二教并重。比如武则天佞佛出名,但也曾宣称“道佛亦合齐重”;睿宗李旦也主张“释及元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明确主张僧道并行。北宋初年,黄老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仍然相当广泛,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太宗赵光义先后征召过道士陈抟、丁少微、赵自然、柴通玄等。真宗赵恒大力推崇道教,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希求神灵保护,著名道士张无梦曾受真宗召见,他的高徒陈景元则被神宗赵顼赐号“真靖大师”。到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徽宗声称天神下降,授意道菉院上章,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把道教变成了国教;他还采纳蔡京的主意,“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使自己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南宋金元时期,道教逐步形成了全真、正一两大道派,北南各据一方。到了明代,“三教合一”成为一种实际形态,比如三教可以共同信仰关帝,《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即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不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等都更推崇道教,而世宗朱厚熜(嘉靖)尤甚,所谓“青词宰相”的出现就是他崇奉道教斋醮的“杰作”。为求长生不老,朱厚熜到处搜罗方士、秘方,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在位45年间,竟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如上所述,较早写到韩愈被贬潮州时开始转变思想的小说是刘斧的《青琐高议》,而刘斧是北宋人,神宗熙宁年间在世(约公元1073年前后)。中经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等元杂剧和佚名《韩湘子三度韩文公》等元南戏的演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王世贞(1526—1590)《列仙全传》中称韩湘子师从吕洞宾,并以“云横秦岭”一联诗的得到验证使韩愈相信了“湘之不诬”。同时代的吴元泰(约公元1566年前后在世),其《八仙出处东游记》第三十一回“救叔蓝关扫雪”,交代韩愈最终被湘子“度”了“仙去”。而旧题“唐瑶华帝君韩若云自撰”的文言小说《韩仙传》及明天启三年(1623)面世的杨尔曾的白话长篇通俗小说《韩湘子全传》,不仅写了韩湘子成仙之事,还详细描述了韩愈被湘子引领弃儒修真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这些小说中韩愈之所以最终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念上发生重大转变,与上述道教受到上层统治者推崇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二是与道教的发展需要有关。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德”即“道”在人及万物中的显现,所以要“尊道”而“贵德”。道散为气,聚则为神,意味着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故道教徒既尊道德,又信神仙。任何宗教都有通过传经布道以求发展的需要,自然也都有相应的一些传播方式。道教的传播方式除了向信众正面宣传道教“尊道贵德”、“仙道贵生”的教义和展示五花八门的道术、举行斋醮等活动为信众提供宗教服务以外,也利用一些文艺形式如法事音乐、青词、道情以及道教故事等,向信众传教。宋元以来,出现了“八仙”的故事,并在元代的神仙道化杂剧中基本成型(马致远《岳阳楼》、范子安《竹叶船》和谷子敬《城南柳》等杂剧中都有八仙)。到明代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八仙”已确定为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汉钟离、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和曹国舅等8人,“八仙”的故事遂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有关八仙度人修真的故事体现了道教“随方设教,历劫度人”的教义,对广大信众来说颇具诱惑力;而“湘子度文公”的故事无疑是体现道教不可抗阻的神奇魅力的一个典型个案,自然是道门所乐于使之传扬天下及后世的。正是出于利用道教故事以强化道教在信众中间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目的,各道教宫观多建有供奉八仙的殿堂,西安还有八仙宫(古称“八仙庵”),其主殿供奉八仙。每逢新春和朔望之日以及八仙神诞之日(传八仙神诞之日,如铁拐李为七月初十,汉钟离四月十五,韩湘子十一月初九等),道教徒和信众则到八仙殿堂奉祀,有关“八仙”的故事(包括“湘子度文公”之类)自然也就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三是不排除或与道门及有道教信仰倾向的文人的某种微妙心理有关。韩愈排斥佛道,为自己赢得了“性明锐,不诡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升黜不改,正言亟闻”等众多美誉,可谓是出尽了风头,赚足了眼球。可这对于佛道及有这方面信仰倾向的文人来说,却不啻骨鲠在喉,必欲吐之为快。而欲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文学虚构的手段让坚决排斥“二教”的韩愈最终还是抵不过宗教的感召力而弃儒修真(或是从佛),如同踢了一脚“乌龙”,把球射进了自家门里。这就既让历史上的韩愈遭受了追加的“羞辱”,为千载佛道出一口“恶气”;同时也利用了韩愈的重望高名,近乎“暴力”地“化敌为友”,巧妙地借以宣传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意识。前文提到,较早写到韩愈被贬潮州时开始转变思想的作家是北宋的刘斧及元代的纪君祥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五十四)说《青琐高议》“所纪皆宋时怪异事迹”,乃作者“侈谈神怪”之书;又据钟嗣成《录鬼簿》,纪君祥共创作了6部杂剧,其中就有《韩湘子三度韩退之》、《陈文图悟道松阴梦》两部神仙道化剧。这表明,刘斧、纪君祥至少都是有着道教信仰倾向的文人。因此,由他们肇端把韩愈说成是一个最终改变信仰、弃儒修真的士夫,就不足感到奇怪了。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见,古代小说中表现韩愈这个人物的流贬心态,作者所遵循的正是设身处地忖度人情事势,以求达到历史影像与艺术真实融于一体的路线。这至少从两方面启发了我们:
(一)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对小说人物韩愈的研究,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里应该主要探讨某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曾经南迁和流寓岭南者(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在古代小说中的人生故事、艺术形象和流贬心态,探讨他们分别被转换成了怎样的文学人物,探讨他们是如何被转换成为文学人物的。毫无疑问,这种探索可以开阔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对于古代小说的题材来源研究、与特定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文学形象的演绎变迁发展规律的研究,无疑都将有很大的帮助和贡献。
(二)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说,对小说人物韩愈的研究,又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韩学”研究的领域。作为历史文化名人,韩愈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古代小说家演述韩愈其人其事,不仅反映了韩愈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且通过他们的演述,广大受众的心里也有了栩栩如生的韩愈的形象。于是,韩愈对后世的影响就产生了两种效应:一种是历史文化名人韩愈对于后世作家产生影响;一种是作家笔下的文学人物韩愈对于历代广大受众产生影响。进一步说,不仅小说中的韩愈需要研究,晚唐五代以迄明清时期流传于民间的戏曲、宝卷、道情以及民间故事等俗文学中的韩愈也要研究。而类似这种有关韩愈影响的研究,目前在学界还留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得好,无疑可以弥补“韩学”研究的某种缺憾。
注释
①(唐)皇甫湜:《韩愈神道碑》,见《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7页。②《旧唐书·韩愈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565页。③⑦(唐)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30页。④⑧(唐)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3页。⑤(明)高棅:《唐诗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35页。⑥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62—64页。⑨《韩湘子全传》第十九回:“宪宗问道:‘此郡既有妖鱼,想是烟瘴地面了,但不知离京师有多少路程?往返也得几个月日?’吏部尚书奏道:‘八千里遥远,极快也得五个月才到得那里。’宪宗道:‘既然如此,着韩愈单人独马,星夜前去,钦限三个月内到任。如过限一日,改发边卫充军;过限二日,就于本地方斩首示众;过限三日,全家尽行诛戮。’”见清刊本《新镌绣像韩湘子全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⑩(唐)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番》,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3页。(唐)韩愈:《次邓州界》,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3页。(唐)韩愈:《潮州刺史上表》,见《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5553—5555页。(唐)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见《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6462页。(唐)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唐)韩愈:《祭鳄鱼文》,见《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5747页。(唐)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57页。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见《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104页。(唐)韩愈:《谁氏子》:“神仙虽然有传说,知尽知其妄矣。”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1页。(唐)韩愈:《忽忽》,见《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1页。(宋)陶谷:《清异录》(火灵库):“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唐)武则天:《僧道并重敕》,见《全唐文》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991页。(唐)李旦:《令僧道并行制》,见《全唐文》卷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页。《宋史·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夏四月庚申,帝讽道菉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20—322页。《新唐书·韩愈传》,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七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867页。(宋)苏轼:《韩文公庙碑》,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508页。(唐)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见《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6466页。
责任编辑:行健中国大片的新转机——兼及视觉转向中电影与文学的联姻